在三国时期文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盘古的传说首次出现。另外,《五运历年记》也记录了盘古创造万物的情节。此外,《中国哲学史》教材引用了这两段资料,对于盘古神话是否反映了中国远古传说的真实情况进行了论证。教材指出:“虽然盘古创世的神话传说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正如吕思勉所说,这一神话故事非常旧,因此广为流传。”基于这一点,推断由于远古时期没有文字,加之我们的祖先有述而不作的传统,所以这一神话内容发生在很早远 古时期,是千百年来中华先民口耳相传的结果。

本土观点认为,公元一世纪时,河南和山东地区就已经有着广泛分布的一些关于盘古的事例,其中最确凿的是公元86年的记录,一些雕像可能早至新莽年代,从而推翻了“盘古来源于印度”的说法。
王晖先生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盤古是上古中國土地神「亳」的音變,並否認盤古在舊代神話序列中最晚出現,而被積薪式地列為時代最早、地位最高的創世主神。他們從中國本土文化中尋找盤古傳說的根源,以及重新將盤 古傳說納入史學考察範圍等方面,有著啟發性的意義。

正如王文中所總結,這些對於盤 古來源的大量討論可以歸納為「本土觀點」與「外來觀點」兩種主要立場。「本土觀點」的支持者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論證。一是多將「盤 古」與「瓠」相聯系,但瓠最初並無開辟天地、創生萬物之類似功績或象徵;二是多運用近代乃至當代收集到的民族學及民俗學材料來論證歷史上的盤 古。在這方面面臨更多挑戰。而持 «外來觀點» 的學者則大都沒有正面回答:如果三國以前沒有盤胡傳說,那麼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中又怎麼解釋天地生成?誰又是開辟和創生的大神?
雙方學者使用基本史料時對史料來源追查不深,使原本有限 的史料定年不清、意涵發掘不足直接影響了對於盤胡傳衍歷程 的正確理解。

除了王晖先生新的論述之外,有主張 盤胡為「盾瓠」的音轉,即由苗族中的盾瓠信仰演化而成的人士,如清人蘇時行《爻山筆話》、《越缦堂日記乙集》,夏曾佑《中國舊代史》,聞一多《伏羲考》等。茅盾認定 盤胡傳說發生於南方,而杨宽則認同但否認其出自苗族,而認為它起源於北方或西北地區。还有主張 盤胡来自 《山海經》的烏陰(烛龍)信仰的人士,如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以及刘起《开天辟地的大明与盘庚》(1988)。
对于“外来的观念”,除极少数主张来自巴比伦文化以外,大多数学者则认为盘胡传说来源于印度婆罗门信仰,并且各有不同。这一点体现在马欢对tman(梵语中的“自我”概念)的讨论,以及高木敏雄对布鲁沙(Brahmā)的研究。但这些观点并未得到充分证明,因为它们都是基于有限且缺乏准确性的小量资料构建起来,不足以作为全面解释历史事实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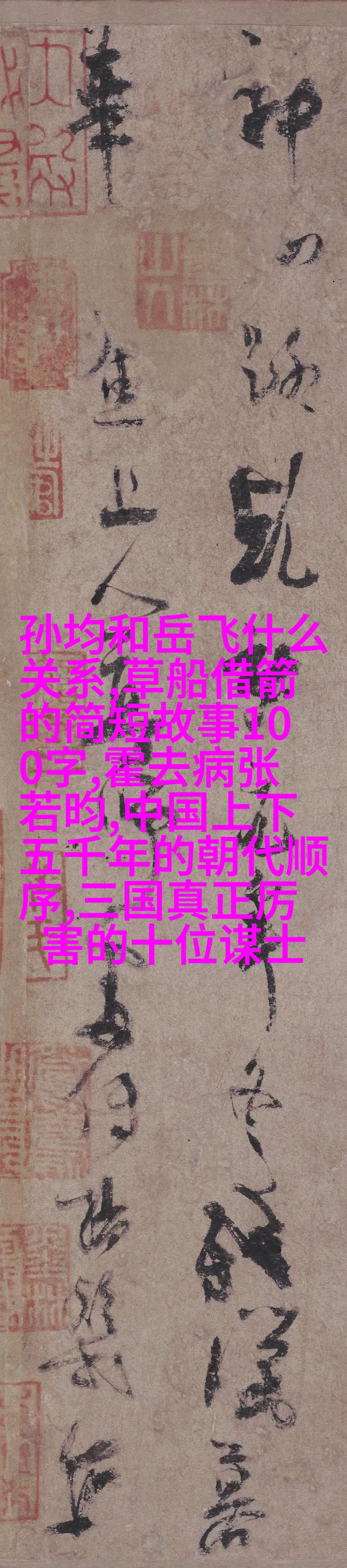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在汉末魏晋间佛经汉译过程中,通过将印度婆罗门教义融入到中国文化体系内,以此方式使得包括绘画艺术在内的一系列宗教符号得以流播和发展。这一点体现在饶宗颐关于安荼论与晋吴间宇宙观以及围陀与敦煌壁画等研究工作中,他们试图揭示如何通过选择性吸纳来形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心理状态,以便更好地适应当时社会环境下的需求。
总结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无法忽视这种跨越时间空间界限,将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共通性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智慧如何不断进步,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背后的脆弱与强大的双重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尊重前人的智慧,同时也不忘发扬自己的创新精神,这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人类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