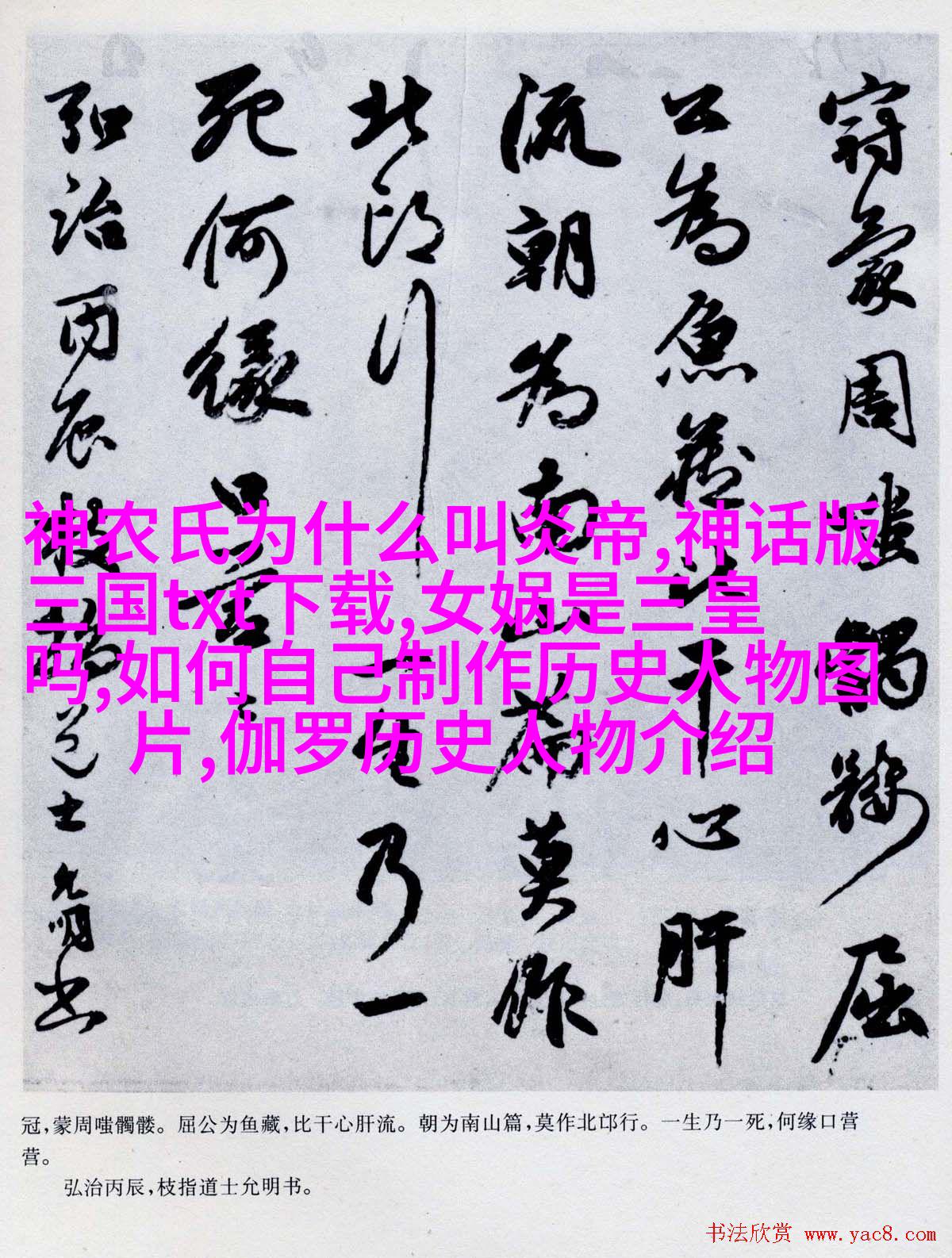在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以其好色和食欲著称。他有正式编制的姨太太七位之多,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姬妾和短期伴侣。为了满足性欲,他必需摄取各种能增强体力、壮阳的食物。食与色的结合,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

当时戚继光守卫登州,他专门指派渔民捕捉一种名为“腽肭脐”的海兽,即俗称海狗肾,将其定期送往北京,以供这位内阁长官享用。据明代文人王世贞记载,张江陵喝下这种汤后,感到奇热攻心、阳亢无比。在风雪寒冬中,他不戴帽子,这成为万历年间京城的一道风景线。
张居正因而成为一个会吃的官员,这并非罕见。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不讲究口福的官员,他们经常被请客、宴会或应酬,被尊到主桌主位。这使得他们嘴巴越来越刁、舌头越灵、胃口越大、品味越高,从而提高了吃法水平,使得厨师的手艺也随之精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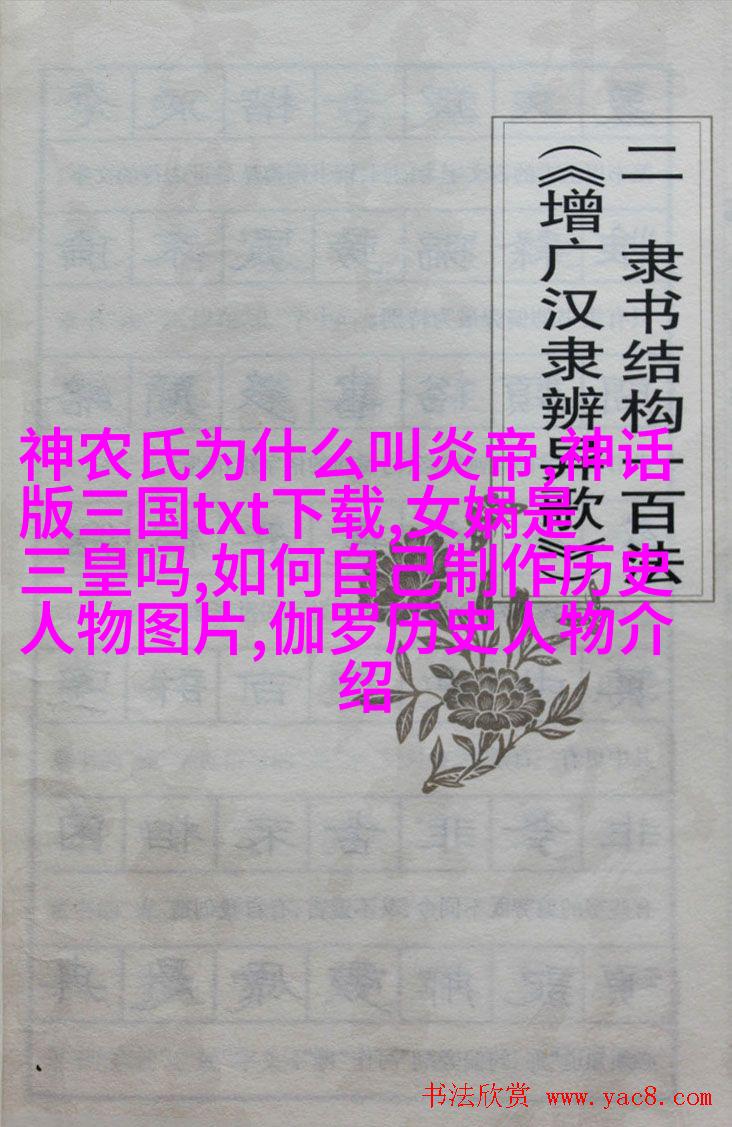
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说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上的人,一日,让她作包子,她却推辞说不能。”士夫质问:“既然是包子厨中的人,为何不能做?”那妾回答:“我乃包子厨中的缕葱丝者。”想象一下,那个时期太师府的大规模厨房,其规模相当于一个营级单位。
清人的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提到,当年羹尧从大将军降职为杭州将军后,其姬妾都散去,只留下一位曾在他的饮馔部门工作过的人。她自言只负责烹调一种小炒肉,每次将菜单呈报给将军,如果点选小炒肉,她就忙碌半日,但几个月里仅出现两三次。她笑着对秀才说:“酸秀才,你想试试吗?但你家的每斤肉都要按斤计卖,从哪里开始呢?”秀才失望地听着。一天,秀才找到机会,把村里的赛神大会用的猪借给了她,她终于可以展现她的烹饪技艺。结果,她带回了一整猪,对自己使用的是活猪,而不是死猪,所以味道应该更佳。但她还是勉强切出一块,用它来试试,最终让秀才先尝,然后自己进入厨房,不久又出来,看见秀才委顿在地,只剩一点气息,再细看,那块肉已经吞入喉咙,并且被吞咽下去。这就是蔡京最终饿死的情况,而年羹尧被罚至杭州看守城门时,即便想要吃根油条,也不得已,可他们各自曾经担任宋朝宰相和清朝将军。这些公务人员拥有能吃、高兴吃、大快朵颐的心态,无论是精致美味还是粗鄙无礼,都无法填补他们永远空洞的大口。此刻,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发扬光大的过程,或许恰恰依赖于五千年的这些大小官僚们不断探索新鲜事物、新鲜口感、新鲜风格,以及不断改良传统菜肴的努力。如果要评功摆好的话,不知道这些善吃之手段掌握者们,是不是该算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